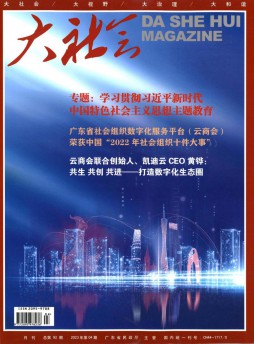社會學理論下的“民族電影”探討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社會學理論下的“民族電影”探討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卡爾•W•多伊奇(KarlW.Deutsch)清晰地闡明了一個最明確和廣泛的關于民族主義中溝通的角色的理論。在其第二版《民族主義與社會溝通》一書的引言中,多伊奇強調與當前爭論有關的一個基本主題:他觀察到民族國家是“處理事務的主要政治工具”,并強調,考慮到民族的彈性,超越民族的整合具有與生俱來的局限性。多伊奇理論的主要命題是:“人們團結在一起的本質——是個體之間溝通的互補性或者說是相對效果——在某種程度上就好比彼此之間的友好關系,只不過規模上更大罷了。”多伊奇認為“人”是民族形成的基礎。反過來說,這與“民族國家地位”不同,即利用政權來追求一個群體的凝聚力及其身份認同的一致性。盡管沒有清晰命名,這一理論蘊含這樣一種理念——那就是“無國家的民族”(thenationwithoutastate)——這一理念既作為一種分析范疇,又作為一種旨在現存的國家國際體系中重新定義民族自治權的政治目標,近年來變得日益顯著。多伊奇認為,對國家權力的使用最終依賴于“相對協調和穩定的記憶、習慣和價值結構”,而這些反過來又“取決于社會從過去到現在及同時代之間的溝通能力”。社會溝通理論包含聚集社會文化群體的方法,以及內聚力形式如何影響制度和社會文化互動。溝通的整合是有重要意義的,因為它生產出社會封閉。爭論的核心就是民族和民族國家強烈地被其社會性溝通互動結構所限制這一觀點:“人們通過這種溝通效果和其成員獲得的溝通能力的互補性而被從內部凝聚到了一起。”民族性因此具有溝通能力和歸屬感的客觀功能。
二、高雅文化、想象的共同體與平庸民族主義
多伊奇關于社會溝通的潛在概念——如果不是他理論上的習語——充其量一半被認為緊密依托于最新的著作,如厄內斯特•蓋爾納(ErnestGellner)著名的《民族和民族主義》(NationsandNationalism)以現代主義的視角對民族主義概念的原則進行了闡述。蓋爾納認為,民族國家的形成是工業化不可避免的結果,伴隨著復雜的勞動分工。工業社會所創建立的社會關系意味著,為了有效運轉,人們原則上需要能夠做任何事,這就需要“通用的培訓”。這種實際知識的傳遞需要一個普遍適用的、標準化的教育體系,適用一種標準化的語言媒介。就是這一過程引發了不可避免的“政策和文化之間關系的深層調整”,即民族主義,“人類群體組織成為大規模的、集中教育的、文化同種的群體”蓋爾納的理論把工業化的解釋模型與典型的多伊奇社會溝通概念聯結起來。蓋爾納認為,文化指的是“特定群體各種風格的行為和交往”,在當代世界中以民族國家的形式呈現。對這種政治形態中的成員來說,“文化現在是必要的共享媒介”。文化的邊界被民族文化所定義,傳播著一種文明(教化)的“高雅文化”,是國家教育系統的關鍵介質。因此,民族文化被官方文化所廣泛定義。這一理論較少關注民族內部的不同和沖突的來源,而更關注是什么讓民族得以凝聚。因此,如同多伊奇的理論一樣,蓋爾納主要關注民族文化如何被創造,而不是如何維系和復興,他同樣強調被民族國家保護的文化的獨立性。因此,盡管多伊奇只是順便被提及,但是作為蓋爾納的跳板來簡略思考媒介在民族文化中角色,實際上他的影響比看起來要深遠得多。
與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McLuhan)相呼應,蓋爾納部分地認同媒介即訊息,但是這一準則考慮到“語言與風格”而被修改了。所謂“語言與風格”即常見的行為準則如何引領觀眾去意識和理解到,他們是某個集體(通過那些常見的行為準則所構造出的集體)中的一員。媒介因此承擔起一個分類體系的功能:公眾對民族空間的普遍認同便被認為是這種文化體系形式產生的影響之一。媒介是分界的標志物,與“蓋在文化上的政治屋頂”密切相關,并使那種文化進入一個民族國家之中。這種說法夸大了一點。“語言和風格”不僅僅是用于傳播它們的媒介,它們與“內容”方面的問題也密切相關。這是文化產業所生產出來的基本要素,也是電影和電視業政策的核心問題。國家對于自身“民族”內容的態度通常在國際文化貿易中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經常體現在民族交流政策中。因此,蓋爾納對社會溝通理論的演繹,重現了多伊奇對溝通共同體內部因素的專注,而不去考慮引進外部的因素和思考外部因素會如何影響內部因素。它忽略了那些能在實質上決定特定民族身份的差異性。
內在論的觀點也貫穿了近幾年另一個重要的文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en)的《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Communities),該書已明確地為大多數近期民族電影的研究提供了理論開端。在解釋歐洲民族的出現時,安德森和多伊奇一樣,甚至比蓋爾納更強調交流媒介在民族意識形成中的重要性。“積極的意義上,半偶然性地但是爆發性地,在生產力、生產關系、技術交流和人類語言多樣性逐漸消失之間,使新的社區成為可想象的。”然而對于蓋爾納的論點,國家的教育系統產生的文化姻親以及聚賢,安德森主要的論點是“印刷語言產生了民族主義,不是一個特定的語言本身”。因此,強調的是在假定合適的物質條件下,在想象共同體建構中傳播媒介的重要性。依安德森所說,“印刷語言”是通過書籍和報紙市場傳播使特定方言標準化的方式。他的描述絕對是古登堡式的:移動影像帶來的影響并沒有被說明。機器復制的印刷語言整合了語言交換領域、固化了民族語言,創造了新的權力成語。安德森稱,“民族主義敘事”與將“歷法意識”作為組織原則的報紙,是塑造民族意識的兩種關鍵媒介。通過協調時間和空間,這些甚至能在民族國家形成之前,就闡明一個想象的民族共同體。安德森思索過民族故事是怎樣經過人口普查、地圖和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在后殖民地國家被講述的。雖然,不是安德森故事中的一部分,但是移動影像對形成后殖民地國家的重要演變作用,已被他人所強調。盡管安德森沒有引用多伊奇的論述,他的方法依然很明顯地處在社會溝通理論的框架中:想象的共同體處在社會文化和民族國家的溝通空間中,它是民族形成主要利益的內部過程。
安德森關于想象的共同體的爭論以一個極具特色的解讀方式被邁克爾•畢利希(MichaelBillig)采納。然而,畢利希強調的民族主義陳詞濫調,就是把民族主義納入日常生活的一些儀式和習慣這個可論證的命題。畢利希認為,在當代世界,所有人只是把所在國家的代表性事物印入腦海。他們國家的國旗每天都在公共建筑物前飄揚,但是大部分都被當成裝飾品;新聞報道將一些大事件分類成國內事務,而與外國的報道區別開;天氣預報強化了人們對政治地理學的認識;體育英雄們體現出民族美德,調動了集體榮譽感;危急時刻,尤其是戰爭,政治領導人要進行愛國主義演講;通過民族語言和歷史的傳達,人們滋生了共同體意識等等。這就是民族認同常規的、不引人注意的、不斷重復的內在支撐。與蓋爾納和安德森一致,畢利希的分析填補了“溝通互補性”的空白,并且強調要牢牢把握住如何對世界進行分類。但值得注意的是,畢利希不像其他前輩一樣,相比于民族是如何形成的,他對如何維系民族更感興趣。
三、民族的邊界與民族電影的范圍
電影研究關注電影在民族中所扮演的角色,必然是內在式的,主要關注的是移動影像的生產、傳播以及消費怎樣構建了民族的集體性。然而,這種內在主義必然被把外在性作為一種塑造力量的認識所調和。的確,民族性實實在在地被好萊塢產品進口到本國的文化壓力所影響,構成了民族電影在當下的問題。這些對民族理念的外部挑戰被解釋為文化、經濟、政治甚至是意識形態。對于蘇珊•海沃德(SusanHayward)來說,她認為如何描述民族電影的這個問題深深根植于政治文化的發展,根植于“關于一個民族多樣而特定機制的神話被創造”的過程,被國家主義范式所深刻影響:“電影的作用在于一個民族文化的融合……電影賦予一個民族語境,而后圍繞一些概念建構一系列聯系,首先,是國家與公民,然后是國家、公民與其他因素……一部‘民族’電影不可避免地被概括成一系列圍繞兩個基礎觀念的闡述,這兩個基本觀念分別是:同一性與差異性。”
在這種建構中,民族被視為單一的,特定國家的電影生產研究審視著“民族電影”。民族電影可通過對電影本身的分析、電影所引發的語篇,及體現在檔案和展覽中的遺產來研究。海沃德的觀點深受法國塑造民族歷史的自覺偏好和與好萊塢長期明確的對抗所影響。“同一性”的概念強調了內向聚焦,而“差異性”的概念通過對比和比較,指明了民族電影的外在因素。對于海沃德來說,分析法國民族電影的可行辦法就在于強調電影生產問題,以及包含在電影生產中的鮮明的電影文體論。莎拉•斯特里特(SarahStreet)在描述英國的情況時,提出了相似的對民族電影實用主義定義,也是最容易實現的,即強調本土生產,也就是理解為“在英國注冊的電影”,考慮到在資金、合作制片人和電影制作創意性人才等方面的多國混合因素,這個定義有很多含混之處。然而,這種簡化被英國風格(Britishness)的接受所調和,成為“一個在日益國際化、互文多樣性的現代電影流派中的元素”。基于相同的領域,安德魯•西格森(AndrewHigson)提出,民族身份認同和民族電影都應該以一個過程化的視角來看。他提出,我們可能會用一些特征來界定民族電影,包括:電影產業和商業,在展示、消費以及對民族文化的影響方面,在文化政策制定和評論界所使用的定義等方面,最后,特別是對(國家)特定流派的支持。西格森接著對這一過程進行了如下描述:“電影經常有助于展現一個國家的民族性。通過植入電影體驗的基本框架,這類電影以戲劇化地表達人們當前的恐懼、焦慮、快樂和愿望,構建了一個將同一個民族的人們團結在一起的想象的紐帶。因此,一個多樣和互相敵視的群體的人們認識到他們是一個有著共同文化的單一體,并與其他文化和共同體對抗。當然,這一點從來沒完全成功過。”當西格森提出應該如何定義英國民族電影并主張電影文化提供一種可以劃分群體的方式時,他也明顯持有政策制定者和民族文化知識分子所推崇卻無法實現的文化保護觀點。與海沃德相反,西格森讓這種爭議與電影的生產脫離,強調觀眾如何消費的重要性。于是,所有的問題都演變成了“觀眾是如何通過多樣的國內外影視作品建立自己的文化認同”。
這一論點也有反駁者。例如約翰•希爾(JohnHill)區分了保護民族電影產業的經濟學觀點和支持民族多元呈現的文化觀點。他認為后者更需要認真關注,因為全球政治經濟交流設定了好萊塢以外電影生產的貿易條件。他認為如按照西格森訴說的,為了強調消費而提升觀眾理解觀看方式的重要性,是對民族電影概念無法成立的利用。希爾特別談到了英國的情況,認為西格森的方法將會使好萊塢電影被劃分為英國民族電影的一部分,僅僅是因為好萊塢電影被英國觀眾所消費。他反駁說,區分“在英國的電影”和“英國民族電影”很重要。保護后者要走向規范化,并認為民族電影應該代表文化的多樣性,它沒有必要承擔民族主義的使命。希爾指出,關于“民族”的同一化觀點在面對英國日益明顯的多樣性的情況下分崩離析了。黑人電影和蘇格蘭及威爾士電影制作對狹隘的英國風格(Englishness)概念構成了挑戰。希爾的觀點可以解讀為是一種請求,目的是保持批判性文化話語在思考電影在民族公共空間中所扮演的角色。盡管與時代潮流相一致,但是將文化生產降低為經濟問題來考量,的確嚴重限制了爭論的可能框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承認消費如何可能構建集體主義身份并不需要放棄關于民族電影生產中文化價值的爭論。相反,它提供了另一個平行的理解電影在民族空間中如何伴隨著標準化和經濟化觀點運行的模式。這一觀點被皮埃爾•索爾蘭(PierreSorlin)所發展。他認為電影在代際的消費是理解意大利民族電影的關鍵,“看電影的四代人建構起一個巨大的對不同聲音和影像的重寫本,國內的和國外的,并用這些在意大利,他們所在的特定地方,來組織他們的生活。他們像欣賞國內電影一樣欣賞美國電影,但是他們吸收和重新使用這些素材的方式是他們自己的,這就是他們挪用不同種類的電影素材來建立意大利民族電影產業的方式”。
這條評論反映了文化是天然融合的。與之伴隨的是,許多當代的拉美人試圖在文化和溝通理論方面思考文化依賴的本質。從根本上來說,這是對文化主導問題重新理論化下,對全球文化的挪用和重組的爭論。索爾蘭概述了捍衛民族電影計劃背后的本質上模糊之處,因為他發覺,一方面,“在它20歲前,電影延伸超越了民族前沿”,但是另一方面,“電影一直被認為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比制造和發行電影的機構和公司更復雜,但從根本上來說,仍是由民族傳統所控制”。當代對于“民族電影”的分析與關于民族的社會學已經確立的思考是完全一致的,因為它們同樣是從根深蒂固的假設出發。社會溝通思考是對一個主權國家、世界民族國家文化地理學的有意識或無意識的表達。這是電影研究的基礎,它在很大程度上衍生于對于民族主義和民族身份認同的社會學爭論,并以此作為民族電影研究的必要起點。其主要興趣在于民族電影現在是或應該是什么,這與建立民族集體性的政治問題明顯相關。民族電影的主要任務就是定義和描述民族與電影文化之間的關系。移動影像不可避免的跨國流動已經成為關注的前沿問題,因為——除美國以外——電影研究總是在努力克服文化依賴造成的后果。
作者:菲利普·施萊辛格
- 上一篇:金融精準扶貧工作站建設方案范文
- 下一篇:社會學的理性化反省與感性論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