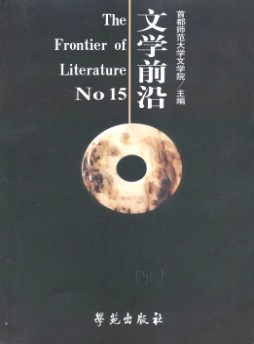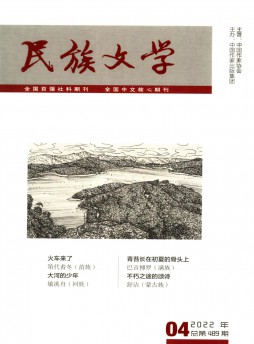談文學(xué)月刊及封面設(shè)計(jì)者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zhǔn)備了談文學(xué)月刊及封面設(shè)計(jì)者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diǎn)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fā)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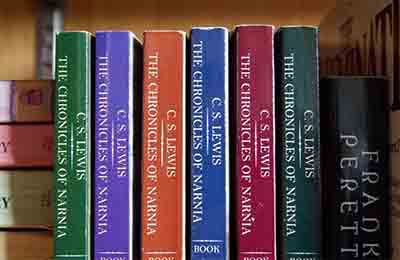
1《文學(xué)》月刊封面抽象風(fēng)格下的潛在語(yǔ)匯
生活書店立于左翼文藝雜志界,應(yīng)對(duì)報(bào)刊檢查制度的方式是多樣的,歸結(jié)起來(lái)主要有三:其一,改換刊物的名稱與封面,如《新生》周刊之于《生活》周刊;其二,真實(shí)的編輯人、出版人不在名單中列出,或頻繁更換作者化名,如魯迅之于《文學(xué)》、《譯文》與《太白》;其三,色彩避免使用大面積的紅色,通過(guò)文字與圖像的包裝使其看起來(lái)更接近于一本商業(yè)性很強(qiáng)的雜志或純文學(xué)雜志。關(guān)于第三種方法,《文學(xué)》月刊可以作為一個(gè)例子。沈永寶先生曾在文章中提到:“《北斗》創(chuàng)辦之初,曾有意辦得‘灰色’一點(diǎn),以保生存。《文學(xué)》更注意保護(hù)色,盡量使它像個(gè)‘商’字號(hào)雜志。此法果然有效。”《文學(xué)》月刊運(yùn)用策略一次次躲過(guò)被查禁的危機(jī),從1933年7月1日創(chuàng)刊到1937年10月共出版9卷,半年編1卷,每卷6期。促成它誕生的因素總的來(lái)說(shuō)主要有兩點(diǎn)。一是話語(yǔ)傳達(dá)的需要。“左聯(lián)”成立后,曾出版過(guò)《萌芽》、《文學(xué)導(dǎo)報(bào)》、《北斗》、《文學(xué)月報(bào)》等刊,但都未久即被國(guó)民黨當(dāng)局禁止。1933年5月,魯迅在申報(bào)《自由談》上的文章受到壓制,不能再發(fā)表了。“左聯(lián)”的文藝刊物,要公開(kāi)地、長(zhǎng)期地出版,已是不大可能了。左聯(lián)的理論家和作家失去了話語(yǔ)表達(dá)的陣地。而文藝雜志是文藝戰(zhàn)線的重要媒介,“‘左聯(lián)’自己辦的文藝雜志已無(wú)法出版,出路何在呢?采取什么政策,什么方式才能不僅繼續(xù)戰(zhàn)斗,而且擴(kuò)大戰(zhàn)線的范圍與影響?”這增加了新型話語(yǔ)媒介誕生的迫切性。二是文化市場(chǎng)的需要。曾經(jīng)的主要載體《自由談》是以文藝性短論為主,不是文藝類的專刊,所以并不合適作為長(zhǎng)久的思想陣營(yíng)。1932年淞滬抗戰(zhàn)以后,商務(wù)印書館的編譯所和印刷廠被炸毀,《小說(shuō)月報(bào)》因此停刊,并且之后也不予復(fù)刊。這樣,當(dāng)時(shí)全國(guó)文壇上缺少了較穩(wěn)定的一流的大型文學(xué)刊物。鄭振鐸因此向茅盾提出了創(chuàng)辦“一個(gè)‘自己’的而又能長(zhǎng)期辦下去的文藝刊物,象當(dāng)年的《小說(shuō)月報(bào)》”的建議。1933年5月6日,《生活》周刊上登出《文學(xué)》的出版預(yù)告:“……編行這月刊的目的,在于集中全國(guó)作家的力量,期以內(nèi)容充實(shí)而代表最新傾向的讀物供給一般文學(xué)讀者的需求。它為慎重起見(jiàn),特組九人委員會(huì)負(fù)責(zé)編輯。聘請(qǐng)?zhí)丶s撰稿員數(shù)達(dá)五十余人,幾乎把國(guó)內(nèi)前列作家羅致盡凈。內(nèi)容除刊登名家創(chuàng)作,發(fā)表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新舊書報(bào),譯載現(xiàn)代名著外,并有對(duì)于一般文化現(xiàn)狀的批判;同時(shí)極力介紹新近作家的處女作,期使本刊逐漸變成未來(lái)世代的新園地;又與各國(guó)進(jìn)步的文學(xué)刊物常通消息,期能源源供給世界文壇的情報(bào)。”綜上所述,《文學(xué)》的封面所需要傳達(dá)的精神也主要包括兩方面:一、代表“最新傾向”與“未來(lái)世代新園地”的時(shí)尚感;二、帶有“小說(shuō)月報(bào)”似的左翼話語(yǔ)陣營(yíng)的暗示。很顯然,前者是圖像視覺(jué)層面的要求,而后者是刊物實(shí)質(zhì)的立場(chǎng),前者因而成了演繹與掩護(hù)后者信息的主要途徑。
2《文學(xué)》月刊創(chuàng)刊號(hào)的封面設(shè)計(jì)者
《文學(xué)》月刊創(chuàng)刊號(hào)的封面設(shè)計(jì)者是誰(shuí)?資料各說(shuō)不一。況早期的書刊封面罕有署名,設(shè)計(jì)者的姓名大多被時(shí)間湮沒(méi)。接下來(lái)筆者嘗試從《文學(xué)》月刊創(chuàng)刊號(hào)的封面圖像入手,結(jié)合出版文獻(xiàn)史料、圖像元素與風(fēng)格考證《文學(xué)》月刊創(chuàng)刊號(hào)的封面設(shè)計(jì)者。陳之佛、鄭川谷都是出版史料與研究文獻(xiàn)中有明確記載的《文學(xué)》月刊的設(shè)計(jì)參與者。莫志恒發(fā)表于1981年《讀書》(第2期至第5期)上的文章《二三十年代的書籍裝幀藝術(shù)漫談》里提到過(guò)《文學(xué)》月刊的封面設(shè)計(jì)者是鄭川谷,遺憾的是,文字并沒(méi)有說(shuō)明鄭所設(shè)計(jì)的是哪一卷的封面,而鄭氏英年早逝,舉辦個(gè)人畫展的愿望未能得償,留下的兩本著作也與個(gè)人著史無(wú)關(guān)。陳之佛在20世紀(jì)20年代就開(kāi)始了裝飾圖案設(shè)計(jì)的學(xué)習(xí)與探索,在“創(chuàng)美圖文館”關(guān)閉之后參與過(guò)《文學(xué)》月刊的設(shè)計(jì),有一部分文章將《文學(xué)》創(chuàng)刊號(hào)也劃入了陳之佛的設(shè)計(jì)作品,但是他們都將《文學(xué)》創(chuàng)刊的時(shí)間錯(cuò)記為1935年。最能代表《文學(xué)》月刊創(chuàng)始初衷的創(chuàng)刊號(hào)以及首卷封面的設(shè)計(jì)者究竟是誰(shuí)?
2.1陳之佛與《文學(xué)》月刊
(1)以從業(yè)時(shí)間與社會(huì)聲望來(lái)看,陳之佛1896年9月23日生于浙江余姚,年長(zhǎng)鄭川谷14歲。1917年編出了我國(guó)第一部圖案教科書;1918年?yáng)|渡日本,翌年考入東京美術(shù)學(xué)校(即今東京藝術(shù)大學(xué))工藝圖案科,成為我國(guó)早期留日學(xué)生中攻讀工藝圖案專業(yè)的第一人,學(xué)成后回國(guó)。1923—1927年間在上海開(kāi)辦我國(guó)第一個(gè)設(shè)計(jì)事務(wù)所——“尚美圖案館”(館址設(shè)在上海福生路德康里二號(hào)),主要服務(wù)于“生產(chǎn)廠家和出版單位”。張道一在《尚美之路》一文中作有具體敘述:陳之佛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一所‘尚美圖案館’,專門為生產(chǎn)廠家和出版單位作產(chǎn)品、書籍等設(shè)計(jì)。現(xiàn)在我們所能見(jiàn)到的他的大量絲綢圖案、封面和裝飾畫等,多是這時(shí)期的作品”。他應(yīng)邀為胡愈之、鄭振鐸等主編的刊物進(jìn)行封面設(shè)計(jì)。《陳之佛年表》記載:“一九二五年,應(yīng)胡愈之之約,為《東方雜志》作裝幀設(shè)計(jì);一九二七年應(yīng)鄭振鐸之邀為其主編的大型文學(xué)刊物《小說(shuō)月報(bào)》作裝幀設(shè)計(jì)。”這當(dāng)中也包括了由鄭振鐸主編的《文學(xué)》月刊。《文學(xué)》月刊創(chuàng)立于“尚美圖案館”歇業(yè)后的第6年。根據(jù)《陳之佛研究》的記錄,歇業(yè)之后陳繼續(xù)進(jìn)行著書刊封面設(shè)計(jì),“他繼續(xù)為魯迅、茅盾、郁達(dá)夫、郭沫若的書籍設(shè)計(jì)的書刊封面,風(fēng)格生動(dòng)活潑,變化多樣。這在‘五四’運(yùn)動(dòng)后的文藝書刊裝幀中,可說(shuō)是異軍突起,深受當(dāng)時(shí)廣大讀者的喜愛(ài),影響很大”。根據(jù)以上史料分析,陳之佛參與過(guò)《文學(xué)》的封面設(shè)計(jì),并且在《文學(xué)》創(chuàng)刊的當(dāng)年,已經(jīng)在設(shè)計(jì)界極具名望,與胡愈之、鄭振鐸等人有過(guò)合作,也有《小說(shuō)月報(bào)》等成功案例的珠玉在前,對(duì)于《文學(xué)》這樣一本經(jīng)過(guò)精心策劃且規(guī)模意義重大的刊物而言,聘請(qǐng)陳之佛來(lái)完成應(yīng)當(dāng)是情理之中的事。
(2)從個(gè)人的設(shè)計(jì)風(fēng)格而言,陳之佛設(shè)計(jì)的封面畫大多為線條柔美的人物和植物等變形紋飾,極注重畫面的細(xì)節(jié)感,刊名文字的設(shè)計(jì)也偏向纖細(xì),多以曲線構(gòu)型為主。而《文學(xué)》月刊的封面畫使用的是較為粗略的直線形構(gòu)型,對(duì)細(xì)部的處理也較為簡(jiǎn)單,僅僅是形與形的透疊關(guān)系而已,并未如他所設(shè)計(jì)的其他畫面一樣加劇線、面的對(duì)比,增加許多細(xì)節(jié)點(diǎn)——《文學(xué)》因此在眾多案例中顯得較為突兀。當(dāng)然,畫面的技法與風(fēng)格并不能成為認(rèn)定是不是作品設(shè)計(jì)者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美國(guó)學(xué)者朱莉亞•安德魯斯曾經(jīng)作過(guò)這樣的比較研究:“《東方雜志》第24卷第7號(hào)(1927年4月)的封面,采用的是古埃及壁畫風(fēng)格的裝飾圖案。《小說(shuō)月報(bào)》第18卷第6號(hào)(1927年6月)的封面,采用的是近似于歐洲19世紀(jì)末‘新藝術(shù)風(fēng)格’的彩色玻璃鑲嵌圖案。兩件為同一出版社、同一時(shí)期的雜志所作的設(shè)計(jì),在題材、手法、風(fēng)格、氣質(zhì)上存在如此鮮明的反差,幾乎讓人難以相信出自于同一人之手。”
(3)從文獻(xiàn)與史料的記載尋找線索。在這一環(huán)節(jié)出現(xiàn)了一些不能相符的信息:袁熙旸(發(fā)表于2006年)與凌夫(發(fā)表于2010年)的文章都將這幀封面用做了陳之佛《文學(xué)》月刊設(shè)計(jì)的圖證,但這兩篇文章都將《文學(xué)》創(chuàng)刊的時(shí)間錯(cuò)記為1935年,這或影響了筆者對(duì)陳之佛與《文學(xué)》創(chuàng)刊號(hào)封面設(shè)計(jì)關(guān)系的認(rèn)定。《上海出版志》在第四編“編輯業(yè)務(wù)”里提到一句,“陳之佛設(shè)計(jì)的《英雄的故事》(高爾基著)、《婚姻與社會(huì)》、《文學(xué)》等書刊的封面均以圖案裝飾為主,色彩渾厚樸實(shí),構(gòu)圖嚴(yán)謹(jǐn)”;在第五編“人物”里并未將《文學(xué)》記入陳之佛的主要設(shè)計(jì)作品中,但陳之佛參與了《文學(xué)》的設(shè)計(jì)這是毋庸置疑的,黃可甚至認(rèn)為陳之佛一生設(shè)計(jì)過(guò)的期刊只有《東方雜志》、《小說(shuō)月報(bào)》、《文學(xué)》等3種;而經(jīng)袁熙旸的不完全統(tǒng)計(jì),截至1949年,陳之佛設(shè)計(jì)過(guò)的期刊約12種;并列出了明細(xì),其中,“《文學(xué)》第1—4卷,1935—1937年,共24期”;而根據(jù)《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圖書總目1932—2007》的記錄,“《文學(xué)》1933年7月1日在上海創(chuàng)刊,1933年7月至1937年10月出版9卷,半年編1卷,每卷6期,月刊”。由此可見(jiàn),《文學(xué)》第一、二卷應(yīng)是在1935年之前出版的。綜上所述,缺乏直接可靠的證據(jù)與資料認(rèn)定《文學(xué)》第一卷封面設(shè)計(jì)的設(shè)計(jì)師是陳之佛。筆者前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查找確實(shí)的資料,但告闕如。
2.2鄭川谷與《文學(xué)》月刊
另一方面,鄭川谷進(jìn)入生活書店的時(shí)間很模糊。在現(xiàn)有的研究資料中,對(duì)鄭川谷生平的詳細(xì)描述十分稀少,籠統(tǒng)的描述又大致差不多。在《中國(guó)版畫年鑒》的《木刻講習(xí)會(huì)學(xué)員十三人生平考略》中記載:“一九三一年八月,魯迅創(chuàng)辦木刻講習(xí)會(huì),他參加聽(tīng)講,并在學(xué)習(xí)期間創(chuàng)作了木刻《湖畔風(fēng)景》和《自畫像》兩幅。之后,他想方設(shè)法,克服經(jīng)濟(jì)困難,轉(zhuǎn)赴杭州,考入杭州藝專預(yù)科學(xué)習(xí)繪畫,后又入西湖藝術(shù)院(當(dāng)年由林風(fēng)眠任院長(zhǎng)——作者注)就讀。約在一九三四年底或一九三五年初,他又返回上海,參加了鄒韜奮、胡愈之、徐伯昕等創(chuàng)辦的生活書店,擔(dān)任書籍裝幀設(shè)計(jì)工作……”而《文學(xué)》月刊創(chuàng)刊于1933年7月,若鄭進(jìn)入書店的時(shí)間是1934年,這在時(shí)間上不能吻合。但從這份資料的措辭來(lái)看,似乎也不確定具體是在哪一年,所以《文學(xué)》出自于鄭川谷之手的可能性也不能被輕易排除。就設(shè)計(jì)風(fēng)格而言,盡管《文學(xué)》創(chuàng)刊號(hào)的封面圖像特征符合鄭氏技法處理的風(fēng)格——“有的封面以色塊線條切割……題材方面,他和錢君匋不同,不用植物葉瓣來(lái)組成,而常用機(jī)械零件形象來(lái)組合。喜歡用赭石、淡棕、橘紅、黑等諸墨色……”但在缺乏明確的資料印證之前,筆者也不敢貿(mào)然將其聯(lián)系在一起。幸運(yùn)的是,筆者在《上海美術(shù)志》第五編里找到了確定的描述:“鄭川谷(1910—1938),近代裝幀美術(shù)家、版畫家……1933年畢業(yè),到上海,在生活書店從事裝幀設(shè)計(jì)工作。1936年赴日本考察,其裝幀風(fēng)格受到日本影響。代表作有……《文學(xué)》第一卷第二號(hào)(屠格涅夫紀(jì)念專號(hào))……”而《文學(xué)》創(chuàng)刊號(hào)與第一卷其他各期的封面是大致相同的。這份資料也對(duì)鄭川谷的設(shè)計(jì)風(fēng)格有簡(jiǎn)要描述:“其設(shè)計(jì)用線、面色塊分割的方法居多,圖案多用直線形,也有用石版畫方法表現(xiàn),形式多樣,構(gòu)圖新穎,色彩鮮明,喜用土黃、姜黃、焦茶、草綠等色調(diào)和宋體的封面字”,這雖與莫志恒所總結(jié)的略有不同,但鄭川谷一生設(shè)計(jì)的書刊封面約有500多幀,是值得去進(jìn)行歸納與研究的。因大部分未注明姓名而無(wú)圖證可查,故結(jié)合以上幾份資料與集得的部分鄭氏作品,將其風(fēng)格特征歸結(jié)為五點(diǎn):一、喜用線、面、色塊分割畫面,構(gòu)圖靈活;二、封面圖形以幾何形體居多;三、多以機(jī)械零件等工業(yè)元素來(lái)造型,畫面中多暗喻勞動(dòng)場(chǎng)景;四、封面標(biāo)題文字多使用宋體;五、設(shè)色多用純度較低的暖色系,如棕黃色系,棕紅色系等墨色。以上是從鄭川谷個(gè)人的設(shè)計(jì)技法角度來(lái)談的,至于這幀封面的設(shè)計(jì)邏輯,筆者認(rèn)為仍有可探討的空間。綜合以上的分析,筆者認(rèn)為《文學(xué)》創(chuàng)刊號(hào)及第一卷的封面設(shè)計(jì)是鄭川谷的作品——時(shí)年鄭川谷剛剛完成學(xué)業(yè),經(jīng)歷與名望雖都不能與年長(zhǎng)14歲的陳之佛相比,但初入生活書店的他即以專門從事封面設(shè)計(jì)的員工身份,被委以重任擔(dān)任了《文學(xué)》月刊的封面設(shè)計(jì)。在一般的情況下,已經(jīng)擁有了自己的設(shè)計(jì)人員的書店,便很少會(huì)再去尋求書店外的自由設(shè)計(jì)師了。在開(kāi)明書店或其他書店出版的圖書中,很難發(fā)現(xiàn)陳之佛的設(shè)計(jì)作品——其中一個(gè)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開(kāi)明書店已經(jīng)擁有了包括豐子愷、錢君匋、莫志恒、沈振黃等知名設(shè)計(jì)師。《文學(xué)》月刊首卷的封面是鄭川谷結(jié)合木刻技法與杭州藝專預(yù)科、西湖藝術(shù)院學(xué)習(xí)成果,進(jìn)行個(gè)人風(fēng)格探索的集中體現(xiàn),他使用了自己偏愛(ài)的造型元素,也受到當(dāng)時(shí)復(fù)合美術(shù)風(fēng)潮與刊物宗旨、觀念等因素影響完成了這次設(shè)計(jì)。
作者:李倩倩單位:四川農(nóng)業(yè)大學(xué)風(fēng)景園林學(xué)院
擴(kuò)展閱讀
- 1談水生態(tài)建設(shè)中的人文因素
- 2談地域性旅游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設(shè)計(jì)開(kāi)發(fā)
- 3電影藝術(shù)論文:談電影與服飾的關(guān)聯(lián)
- 4談紅色旅游文創(chuàng)產(chǎn)品設(shè)計(jì)探討
- 5談信息技術(shù)在水文勘測(cè)中的應(yīng)用
- 6談石窟文創(chuàng)產(chǎn)品博物館營(yíng)銷與網(wǎng)絡(luò)傳播
- 7談護(hù)理專業(yè)學(xué)生人文關(guān)懷能力的培養(yǎng)
- 8談立足人文素養(yǎng)促進(jìn)協(xié)調(diào)發(fā)展路徑
- 9談護(hù)士護(hù)理專業(yè)價(jià)值觀和人文執(zhí)業(yè)能力
- 10談人文護(hù)理在高壓氧護(hù)理中的重要性